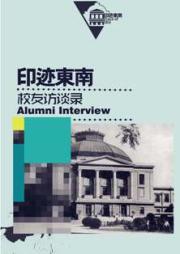
在校团委组织的本科生社会实践活动中,由电气学院聂钢柔、文学院李静妍等来自多个院系的14名2013级本科生,于2014年暑期前后开展“印迹东南”主题活动,通过直接采访东大优秀校友,还原他们的事迹经历和他们在学习生活工作中的宝贵经验,以给予东大当代学子积极正确的引导,激发学子们的爱校之情、兴校之心,让东大学子大学生活更加充实和有意义。
在校友总会的推荐和支持下,“印迹东南”小组的同学们对北京、天津、广东、湖南、海南和南京等地区的23名校内外校友代表进行了面对面的采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校友总会将陆续发布“印迹东南”活动的全部校友访谈录,以宣传校友,启迪在校生。

受访者:樊和平 毕业于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 现任东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采访者:李静妍 聂钢柔
采访稿整理:李静妍
李:樊老师,您好。请问您还记得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报考东南大学吗?
樊:我们这代人和你们这代人非常不同。你们能够自己主观能动地选择报考哪所学校,而我们却是被动选择。我报考大学的时候是1977、1978年,那时中国已经10多年没有高考了,面对恢复高考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我们没有太多的准备,也没有太多的选择。我那时的经历是这样的:十五岁高中毕业,过完十六岁生日就到一个农村中学做老师,班上大概有一半左右的学生年龄比我还要大,做班主任、教语文、政治、化学课程。两年后,被杨根思(抗美援朝时期的特级英雄)乡(当时叫公社)的党委书记、老革命陆健看中,调到乡里做党委秘书。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们只知道可以考大学了,但是各种大学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很多人都是不知道的。记得当时我问别人报考什么样的大学被录取的可能性大一些,回答说中专比较好考,于是我就报考中专。当年高考分初试和复试,初试合格进入复试的时候,我询问读完中专大概会从事什么工作,回答说做工人,于是我就决定放弃,1977年高考就这样结束了。1977级和1978级只相差半年,半年后参加1978级的考试,我当时志愿中没有东大,因为不知道东大还招文科,那时东大叫南京工学院,非常有名,名气至少不在南大之下。当年我考了385分,应该是挺高的分数吧, 可无论如何就是等不到录取通知书,其他三百分以上的考生都已经进大学了,当时的心情可以想像。中秋节前夜,农历八月十四的晚上,我在党委会上作记录,旁边一个领导对我说“听说你被南京工学院录取了。”我当时只是一笑,根本没有在意,因为关于我的消息流传太多了,已经不相信了也不在意了,只是想着明年再考。第二天因为是中秋节,便上街买点肉准备回家过节,一进门那卖肉便跟我说“樊秘书,听说你被南工录取啦?”我心里头一愣,心想一个卖肉的都知道,那可能是真的了。于是急忙跑到邮电所,问有没有我的挂号,所长说有,是教育局来的。打开一看,确实是南京工学院发来的录取通知书。原来东大当年恢复文科招生,著名哲学家、系主任萧昆焘先生预先扣留了一批高分学生,但因为没有批文,通知迟迟不能下发,这样我们的报到就晚了大概一个多月。
李:那么您能否描述一下您进入东南大学、当时的南京工学院的学习生活吗?
樊:好的。还记得当年我们的文科生两届共有72个人,系主任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常有些自得地说:“孔夫子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我现在也有七十二个弟子”。当时我们需要学学科很多。比如数学,当时东南大学的数学教材是上下两册,系主任说我们培养的学生应该比工科数学要求更严格,于是又把南京大学的数学老师找来,我们又学了南京大学的理科数学,那一年仅数学作业我就做了十本。再如统计学,南京大学统计系的主任吴可杰先生给我们讲统计学,他是非常有名的统计学家。而中文,是南京大学中文系著名教授、著名书法家候镜昶先生给我们讲古代汉语。再如政治经济学,我们也学了很多,有120学时。我们当时的培养模式和现在人文学院的模式比较相似。第一年、第二年是不分专业。前两年的知识面很宽,到三年级的时候才开始分专业,分成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自然辩证法四个专业。
李:对于分流专业您有什么看法吗?您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呢?
樊:对于专业,我们和你们的不同可能在于你们似乎预先有一个自己的兴趣,而我们的学习和我们的分配一样,都是被安排的。国外的培养理念中有一个理论,说好的努力和天资不如一个好的兴趣,兴趣当然很重要,但我觉得中国传统中有一些很优秀的东西,专业选择也是如此。我们不光是要改变世界,同时也要改变自己,要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你们现在能够对专业做出主观判断,但专业设计是不是和对未来的人生规划完全吻合也很难说。我相信人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最重要的是当你做一件事情就要把它做得很好。马斯洛提出自我实现理论,很多人认为自我实现就是要充分实现自己,其实不是这样的,自我实现理论的真义是说,做什么事就做得卓越,这才叫自我实现。我们当时没有选择哲学,但照样能够把哲学学得很好。
李:我们在进入大学之前会对大学有一种憧憬,那么您的憧憬是怎么样的呢?
樊:如果说憧憬,你们是憧憬的。而大学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梦,而且是一个天方夜谭的梦,因为当时进入大学是需要通过推荐,而且几乎只有工农兵学员有被推荐的机会。我记得我做中学老师的时候可以每个星期天到当地的一个师范学校进修,有一天晚上我站在师范学校自习的教室的门口,看到教室明亮如昼的灯光,看到教室里的学生埋头苦读,我非常非常的羡慕,我想自己如果能够进入这样的学校来读书的话就实在太幸福了。当时我的梦只能做到这里,做到师范大学,根本梦想不到我能进入东南大学,进入南京工学院。当然当时也不是完全没有上大学的可能,我当时同意由中学进入公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公社工作的话被推荐上大学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李:那么进入南京工学院的大学生活是否符合您的憧憬与渴望呢?
樊:以这样的渴望进入大学,我们这代人的学习,不叫做认真不叫做刻苦,叫做疯狂,疯狂地用功。比如,我们常常不回家吃午饭,就在教室里吃两个面包当做午饭。其实中午不回家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当时自习教室是有些紧张的,如果我们背着书包离开座位的话,下午来可能就没有位置了。因此我常常我早上就到教室了,到晚上才离开。因为因为我回去的比较晚,同宿舍的同学大多已经睡了,我害怕晚上怕惊动同宿舍的人所以在晚饭的时候我就要洗好脚,晚上回到宿舍就睡觉了。还有我记忆很深的一件事情,我们是东大的第一批文科生,所以文科的书籍很少,我记得我当时借到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但是只能借一个星期而且在外面是买不到的,于是我在一个星期内把整个书都抄下来,。抄好的那个晚上我把书包放在教室里占座去吃晚饭,晚饭回来我发现书包不见了,抄好的书是在书包里的。我们当时的学习状态大概是这样,我们当时学哲学是学原著,老师告诉我们只要能把费尔巴哈背下来就能得高分,于是我们当时就都把它们背下来了。因为当时我们对于什么是哲学是不太清楚的,我们只能下功夫、下死功夫,就是做一个信息录入,需要把一些概念、原理输入到大脑里去,方法就是把它背下来,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硬功都是那时候打下来的,。
李:您认为自己在大学生活中让您感到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或感受是什么呢?
樊:实际上我们的大学生活还是蛮枯燥的,没有你们现在的大学生活丰富,我们是教室、宿舍、图书馆三点一线,星期天也是全部用来学习的。我们在学习上吃了很多苦,但是我们也受到了你们这代大学生感受不到的万般宠爱,我们大学生当时就感觉自己是一个城市的大熊猫,尤其是作为东大的学生,因为中国十年没有大学生了,大学生非常稀缺。我们那时候别着一个南京工学院的校徽上街,营业员对我们都是非常客气的,全市民对我们都是很恭敬的。也许你们认为搞各种各样的活动才是深刻的记忆,而我们的记忆是,我们当时上一节课下来,凳子就沾到你的裤子了,是因为凳子上的油漆化了。我还记得当时我天不亮就会起床,天蒙蒙亮就到操场上去读外语。还有我们也需要做很多课堂笔记,比如西方哲学这门课,我们上课基本要把一节课的内容记录下来,我有对这个课作一个统计,我做了抽样平均,我每节课平均一分钟45个字。一分钟写45个字是可以的,可是一节课下来每分钟45个字的上课的强度是很大的。
李:这样看来,当时的大学生被整个社会寄予了非常高的期望,而大学生也是努力发愤图强的,关于当时的学习状况,您是否愿意与我们分享更多呢?
樊:好的。我把学习分成记和忆两个阶段,上课和读书是记的过程,走到教室外面去回忆便是忆的过程。而最诗意的,最美好的记忆是:在皑皑的白雪中,我穿着大衣,穿着一双棉皮鞋在校园里散步。整个校园银装素裹,像一张白纸,一个人走进去,每一个脚印都非常的深,好像整个世界就是你,你就是整个世界。大雪刚刚过后的校园非常安静,你在雪地里走一步一步慢慢地走,你能倾听到世界最美好的声音就是自己脚下皮鞋和雪地摩擦发出的,轻微的,沙沙声。我一直认为你们比我们优秀,我们那个时代大概一百个人中有一个大学生,但是这是因为一半左右的人连高中都没有条件上,我们的优秀是建立在大部分人都不优秀的基础之上,但是你们现在,家长把你们每一个人都培养的很优秀。但正因为我们是从那样一种渴望中走出来的,我们非常懂得珍惜,我们非常注重成绩,那个时候就在市中心的四牌楼读书,但是我们几乎不上街,学校就是我们的全部世界。而你们对于成绩更豁达一些,我觉得这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快乐吧。
李:那么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工作之后的经历吗?
樊:那时候系主任说会留下我们之中成绩好的同学。我在哲学专业中可能是学分绩点最高的,我印象当中我只有两门课大概考了八十几分,其它在九十分以上,但是我没有留校。至于原因,应该是多个方面的。东南大学曾经领导了一个学潮,我们系至少是这个学潮的主力,后来基本上把长江一线牵连进来了。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的学生都很有才,比如讲学校伙食不好是以漫画来表达的。比如画了一个女生端着一碗稀饭,女孩看着倒影倒到稀饭里头说自己又苗条了,稀饭里有倒影那就是稀饭很稀了。而画男生是画一个男孩一直拉腰带,拉到腰带的孔不够了。我们当时没有其它的动机,就是抱怨食堂伙食不好。那个年代的工作是计划分配的,我们那一届分配的不是很好,我被分配到扬州大学。后来我们系主任写信说一定要我回东大,甚至他本人也到扬州去,但扬州大学不同意我回东大。后来扬州大学为了把我留住,把我爱人调到扬大。扬州大学的相关负责人对我说“你可以安心读书了,我们有人质在手里了。”后来我研究生毕业,两个学校的党委书记谈判,据说谈了几个回合。我到现在都非常感谢扬州大学的书记,到最后他就说樊和平这个人留在我们这可能太可惜了,还是留给东大吧。留下来就是艰难创业的历史,当时东大的文科只有两个系,一个是哲学系,第二个是社会科学系,社会科学系是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我们当时拿下来第一个硕士点,科技哲学,是非常不容易的,社会科学系拿下整个学院的第二个硕士点。文科开始很小,我大概是1988年12月左右做哲学系的系主任,一开始的创业过程十分艰难,研究十分艰难。比如中国伦理,我三年备了三次课,第一稿写了60万字,第二稿压缩到30万字,第三稿是40万字,我到现在都留着这些手稿,这些手稿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非常不容易。因为当时工作比较多,要做学生工作,要有很多课要上,要科研,平时是没有多少时间的。因此到了假期,就开始艰苦的创作、写作。我对自己的规定是一天写一万字,我写我的第一部书《中国伦理的精神》的时候正是六四学潮,但关于这个学潮我当时几乎不知道,因为我潜心在家里写作。现在你们看到的我的前期的书的最后署有东南大学水帘居,这是因为当我这部书快写完的时候,楼上面的一个小孩倒了一盆水下来,我正坐在窗口,这个水正好倒到了我写的书上,稿子都打湿了,因为这是一盆水倾泻而下,我就突然联想到了《西游记》中的水帘洞。而且我当时的住所就在一间水房旁边,我家的墙壁都是潮湿的,我为此自己还手工做了一个阁楼,也可以放一些书籍之类的,我到现在身体一直不太好与长期在潮湿的环境中工作是有很大关系的。写第二本书的时候,天气很热,而且是没有电风扇的,我用一块湿毛巾围在脖子上,脚下放一盆水,脚踩在水里,就这样写作。一个星期以后,脖子上全是痱子,很多年我都习惯性的长痱子,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一开始的研究就是这样做出来的。我第一次生大病就是在写书的时候,是写一本书写到到第十八天的时候,就倒下来了,我站不起来但是大脑非常清醒今天写什么明天要写什么。我想,我今天不写,我明天肯定要写。但第二天还不行,我想我后天肯定要写。我们这代人基本上都有这种经历。你们总讲,快乐学习,快乐研究,其实你们要想做出学问来,是能够获得快乐,但那种快乐是不一样的。我感到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听笔尖的沙沙声,你们现在可能很难感受到。你们现在听到的是键盘的声音,但你们永远也感受不到笔在稿纸上的非常迅速的移动的那种沙沙声,那种美好,非常轻微而非常清晰。你能够感受到笔和你的思想的合拍,思想的每一个音符都在你的手上体现出来,你感到这个世界是一体的,你的思想在你的笔端体现出来,不仅是是没有距离的,而且是没有速度的。笔就在驰骋疆场,在演绎你的的思想,在演奏一种乐章,这个乐章非常唯美,你只能用心去听它。不是听之于你的耳,而是听之于你的心;不是听之于你的心,而是听之于你的气,这就是一种学问之美。你感受到这种美以后,你就会非常快乐。再后来的研究中用电脑,也有一种美感,但是之前的美再也找不到了,我打五笔字是比较快的,但我总感觉跟不上思想。什么叫做学问的快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验。一个人学习也好,做学问也好,如果没有感受到学问之美,这是非常可悲的,这说明你没有真正的、全部身心的和它无间道的连为一体。比如我现在写作是目中有人,手中有神,我明确知道我的读者群体是什么人,我不能放任我的思想,,我要时刻拉住我的思想的野马,朝着我预定的目标走,一路上风光无限,但是我不去留恋这种无限风光,我只有一个念头,我要达到那种目标。我1992年成为教授,三十二三岁的时候成为教授,成为当时哲学伦理学中中国最年轻的教授,这个记录保持了五年,不是五年中没有三十二岁的教授,而是到我三十八岁的时候仍没有比我年轻的教授。我记得当时坐软卧都要有工作证的,软卧肯定要教授以上级别才能坐,有好几次在火车上当我把工作证拿出来的时候,那些乘务员都十分吃惊,根本不相信还有这么年轻的教授。不过最年轻教授这个记录不好创造,它意味着你要为东大做很多很多。当时有人对我说“你在东大已经做到顶了,你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赶快换个工作,东大这个天地太小。”我曾经也动过这个念头,但我后来想通这件事情,学校既然把这么好的资源给了我,就到了我为东大做贡献的时候了。我觉的我能把舞台搭多大,我就能跳多大的舞。三十四岁的时候我拿下伦理学的硕士点,当时中国没有这么年轻的人拿下硕士点,一般的都是五十岁左右的人拿到硕士点。那一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学讲学,当时深圳大学的校长派他的办公室主任把我拦住,说香港大学邀请我来创立香港大学哲学系,直接把我接到他家,他的夫人跟我说“你是我们家迎接的第一个客人”。同时他的人事部长到了我家动员我夫人让我们到到深圳去,他们还给我们看承诺给我们的房子。我想到自己去香港大学讲学之前东南大学的校长把我找过去对我说:“你可能没有过去的路费,这个路费我来出。”因为当时去香港的路费要个人来出,但我当时没有这么多的钱,我们当时只有七八十块钱的工资。所以我当时就跟那边的校长说:“我是拿着校长的钱出来的,我不能做背叛校长的事,这是我的伦理。”如果当时校长没有给我出这笔路费的话,我很可能就过去了。后来开始创立博士点,这个过程就更加艰苦了,到1996、1997年全国只有两个博士点,一个在人民大学,一个在湖南师大。当时我们宣布要打点的时候,遭到了非常多的质疑,在学术界我是个草根。让我印象最深的是1993年韦钰校长到教育部去做副部长的时候,当时召开一个伦理学的国际性的讨论会,他看到邀请学者的名单上面没有我,就问“为什么不邀请樊和平来”,教育部才赶快给我发邀请函。我在会上的发言引起了国内外一些专家的注意,当然可能与我当时非常年轻时有关系的,当时全国的教授都是很少的,何况我是那么年轻的教授。而对我刺激最大的是我发现,那天下午有很多专家对我感兴趣,但吃晚饭的时候参加会议的那些中国的老专家把他们的弟子一个个介绍给国外的专家,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的站在那里,我感到自己受了很大的委屈,这是我一生中感到的受到的委屈最大的一次。就在那一天晚上,我下定了一个决心,为了我们的弟子今后不再受像我一样的委屈和屈辱,我一定要在东南大学打下一片江山。1993年有很多人邀请我从政,清华大学组建文科想邀请我过去而且给我的待遇非常好,但是我都没有过去。结果是我们打下了博士点,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复旦大学都没有打下来,所以我们就成了全国第三个点,也是东大历史上第一个土生土长的博士点。有一次学校因为一个评奖让我做一个关于我个人的总结,我大概回忆了一下,我创立了十个全国第一,这个领域的很多全国第一都是我们东南大学做到的而其它很多大学都没有做到。比如说,全国最年轻的教授,全国最年轻的硕士点的创始人,全国最年轻的博士点的创始人,教育部颁发的伦理学是第一个优秀青年教师奖,伦理学第一批长江学者,伦理学的第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年轻专家。现在我回忆起来常常有后怕的感觉,可能我没有勇气重新走过。现在东大六个文科学院,有四个文科学院是从人文学院走出来的。
李:接下来我们想要听一下您对一些社会现象的看法。
樊:好的,我很愿意和你们分享。
李:请问对于大学的绩点您怎么看呢?
樊:我其实不太懂得如何计算绩点,但是我想和我们那时候的分数是一样的。学生必须要重视绩点,虽然不能唯成绩是论,但是学生不重视成绩就像农民不重视收获一样,毕竟成绩与收成那是一个标准。前几名的学生不一定是最优秀的学生,死记硬背当然是不好的,但是这不能成为浮躁的理由和借口。我们必须要扎扎实实地把基础打牢,如果一个考试是公正的,如果考卷是足够有水平的,那么成绩可以成为一个标准,起码是重要的标准之一。我们总说成材,成材就是说你到了一定时候,做你大概可能做的事情,就是成为一个有功能的东西的原材料,一张纸不能够成为一张桌子,但是木头能够使自己成为桌子的原材料。我不担心现在的学生过于重视绩点,我是担心你们过于不重视绩点。我不认为我们学院依据绩点分专业是好的,但是我不能找到更好的办法。按照我理想主义的做法,你们喜欢哪个专业就去读哪个专业,我不去限制,甚至一个学生拿到几个学位,但是现在这个体制不允许我这样做。我能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去保护你们的兴趣,但是你们要做的,就是你要保证你的兴趣是稳定的。我们那个时代不够重视兴趣,因为我们必须要进行信息录入,但是你们现在什么信息都不录入,这不是硬功夫。我认为好的博士生是能够扛着一支笔走天下,不需要图书馆,不需要网络。当年汪曾祺毕业之后给沈从文写信说自己因为找不到工作不想活了,沈从文说“没出息,你有一支笔怕什么。”我觉得文科的人就应该有这样一种本事,你有一支笔你怕什么。我们现在离开图书馆,离开网络就不能创作,这是因为大脑储存的太少,硬功夫不够。你们比我们见多识广,但也许我们能做到的你们不能做到,所以如果你们能把我们这代人的刻苦等很多优点集中在自己身上,你们将非常优秀。
李:现在我们一些学生认为读大学就是为了找工作,一些专业因为工作好找变得热门,一些专业因为工作不好找而鲜人问津,请问对这个现象您怎么看呢?
樊:如果一个大学生的理想就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那么他不会有很好的前途,大学生不能以找工作为自己的理想和报负,应该以一种我想要什么样的人生作为自己的目标。谈到专业的问题,现在绝大部分人的工作和他的专业没有关系,所以在大学中培养一种素质就非常重要,要有一个良好的素质,以不变应万变。在全世界教育都是一个社会分层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对大部分的人是这样的,一个低学历的人有可能成功,但是成功的几率远没有高学历的人高。你们不能目光太短浅,不能为了赚钱而学习。实际上,在中国有很多不应该赚钱的专业赚了好多钱,比如经济,比如法律。尽早给自已一个方向,你想要的生活是是什么,你想要的人生是怎样的。
李:一些人说当代大学生缺乏信仰,对这种说法,您怎么看呢?
樊:我不会批评地去看待我们的大学生,一方面因为他们很优秀,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另外一方面因为我觉得我们总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去看待他们是不够公平的。我认为说中国大学生缺少信仰太武断,如同希拉里说中国人缺乏信仰太武断一样。没有信仰还能够活下来而且能够活得不错,就说明有一种替代,有一种能够把自己安顿下来的东西。如果中国人不能够把自己安顿好的话,你可以说中国没有信仰,但中国人生活的很好。你可以说没宗教信仰、没有政治信仰,但你不能说中国没有信仰。比如文化信仰,比如伦理道德,比如某种坚持,我们是有的。我觉得我们的学生缺少一种引导,缺少一种一以贯之的东西,所以需要激发你们去开拓,去创造,我们应该坐下来和大学生来商谈,遇到一些曾经没有遇到过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面对。我们应该学会在年轻人面前更谦逊一些。
李:那么请问您能认为我们当代大学生普遍欠缺的有什么呢?
樊:你们很难体会到我们那一代人的一些感觉。比如我在做中学老师的时候遇到的一位班长,他没有父母而是和自己的叔叔生活,而这个叔叔是眼睛看不见的。那时候他的学费书费是全免的,但是你依然能够想象到他的艰难。你们现在对于很多东西,没有一种稀缺感,没有稀缺感就不懂得珍惜。另外,你们这一代人缺少故事,学习是你们成长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任务,尤其是你们大多是独生子女,不可能有像我们那个年代的,比如和姐姐妹妹抢一点菜吃的记忆。我们现在要把很多事情解释清楚,不仅要解释清楚而且要搞明白到底对我有没有好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理性能力非常强大,所谓理性就是给一个道理的能力,但是不能够和别人在一起,现代人的孤独也是以前所没有的,所以对你们这一代人来说,如果不能培养出一种伦理能力,那将是非常可怕的,伦理能力就是和别人在一起的能力。
李:您怎么看待一些大学生频繁跳槽的现象呢?
樊:我对这个问题没有考察过,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全世界都不喜欢频繁跳槽的人,在某些发达国家,在几年之内跳槽3次就没有人要你了。跳槽比较频繁一方面与我们的心智的不成熟有关,另外一方面与我们社会的一些机制不健全有关。一位国学大师讲过一个故事是说你走进一个剧场看到黑压压的一群人,看到他们而不同他们交流,其实还不如安静坐下来和一个人好好交流。你面对一个职业倾入自己的情感和智慧去做,相信自己总会有收获。最可怕的是你想得到一切,一切都不喜欢你。你们这代人大多不会委屈自己,我们会委屈自己,我们虽然吃亏,虽然吃了很多苦,但是我们还会坚持把它做下去并且做得很好,哲学专业不是我选择的但是我也做好了。你们总认为有一个天生适合你而且天生你喜欢的人、的事情,但是这几乎一定是你有了过高的期许。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教育的失责,我们对大学生教育太多,关怀太少。刘心武写过一篇文章讲在美国的一所大学一个校长发起的一个“在操场上喊出你最想说的话”的活动。一个华裔女孩大声喊“我是美国人”。后来学校方面了解到这个女孩定了一件文化衫,文化衫上写着“杀死母亲”,原因是这个华裔女孩的母亲把这个女孩放进一个贵族学校,但是贵族学校中只有她一个黄种人,她在学校中都没有人和她玩,她就把受到歧视的怒气撒到母亲身上。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校长意识到了对这个女孩的歧视,于是带领全校学生向她道歉。这在中国的高校恐怕是难以想象的。我们的教育确实要改革,要关心学生更多一些。我总对学生有一些歉疚感,你们都非常优秀,我们对你们关心太少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提供一种根据学生优秀程度来选拔和帮助学生的制度。你们目光要更远一点,不要为了一份工作来读书。
李:最后您能否给我们当代东大学子一些寄语呢?
樊:我现在有一种意识,我们大家要一起成长,因为世界变化太快。变化太快不一定是好事,有人认为变化对于经济是好的,不过变化过快是否对经济是好的也是需要讨论的吧。所以我们这个世界需要两种人,一种人需要不断追逐变化,你们年轻一代可能就是希望走近变化,另一种人总在坚守一种不变的东西。这个世界就成为既是动态的,又是有永恒的。你们年轻人在追求变化追求上进的同时,要更厚重一些。
李: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樊:也谢谢你,今天辛苦你了,也谢谢那位摄像的同学。




